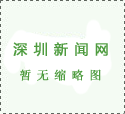在2025年秋日的新疆喀什地区,胡先生作为亩红枣地的合伙人,此刻却只能看着白某某的亲家张某某雇佣人员采收果实,这场从2019年开始的合伙生意,如今面临着法律文书上的“驳回上诉”和眼前这片熟悉又陌生的枣林。
2012年签下《土地承包合同》时,白某某或许没想到这片400亩的荒地会成为日后纠纷的核心,合同里“长期不变”的承包期限和每亩300元的承包费,让她在七年后看到了盘活资产的可能。2019年春天,当她以“赎回被丈夫出售的土地”为由找到胡先生时,这片已挂果的红枣林正迎来第一个丰收季,白某某先行投资一百万,胡先生随即拉来李某某,两人共同投资一百万,2019年签署的合伙协议上,明确写着“共同经营、共负盈亏”八个字。
签约后,李某某70万元的转账记录和胡先生30万元的补款(后补另增利息五万),以及白某某亲手写下的收条成为合作信任的见证。2019至2021年的银行流水里,案外人账户的转账记录清晰记载,2020年12月五十余万元、2021年八十余万元,每笔款项都备注着“红枣分红”,“那时每亩能产550公斤灰枣,每公斤收购价6元,扣除成本纯利润每亩1300元。”
转折发生在2022年初。当胡先生因替白某某借款五百余万担保责任,面临失信风险时,他没意识到这场担保会成为合作破裂的导火索。2月,他在红枣地门口与白某某发生肢体冲突,派出所调解文书里“因合伙经营纠纷引发撕扯”的字样,为后续纠纷处理埋下伏笔。
2023年3月,白某某“胡先生不履行管理义务”起诉请求解除合伙协议,“开庭时她突然拿出两份合同,我当时脑子都是懵的。”庭审现场,白某某出示与张某某的约定“长期租赁”的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》,以及彭某10年租期抵偿100万元债务的《协议书》,使其对合作关系产生重大质疑。两份合同承包价格分别为350元/亩和500元/亩,价格低于同期村委会标准,而胡先生在两年才后得知此事。
“她亲家是张某某,彭某是她二十多年的朋友,这是否涉及利益关联值得探讨”,当地地区法院判决认定:“白某某未经合伙人同意擅自转让,构成恶意违约,无权解除协议”,驳回其诉讼请求。该判决首次确认胡先生等人与白某某的合伙关系合法有效,但未涉及承包合同效力,胡先生认为此判决“守住了合伙权益的底线”,但未料到后续判决对行为的认定急转直下。
2023年5月,胡先生等人起诉索要2022年的56万元收益,当地地区法院判决认定:“2022年土地由张某某、彭某实际种植,收益为承包费共17万元”,按50%比例判决白某某支付八万多元。对此,当事人反驳:“2022年实际仍由白某某委托他人代管,承包合同是名义签约,实际收益未转移”,但法院未采纳其主张。喀什某法院二审维持原判,理由是“承包合同已生效,收益按实际流转金额认定”,当事人认为收益认定存在差异,按每亩550公斤产量、6元/公斤收购价,400亩地毛收入一百多万元,扣除每亩2000元成本,纯利润接近六十万元,法院以“转租费为实际收益”的认定,让他们觉得“像是被人抢走了庄稼,还按青苗价赔了钱”。
2024年,胡先生等人因怀疑恶意串通而起诉要求返还土地、确认承包合同无效并赔偿88万元损失,当地地方法院判决认为:“张某某、彭某属善意取得,承包价格高于村委会承包价,合同有效”,法院特别指出:“胡先生未能证明张某某、彭某知晓合伙关系,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”,尽管证据表明“白某某仍实际控制土地”,但因无证据证明恶意串通,转包价高于村委会承包价为由,诉求被尽数驳回。
庭审结束后,胡先生得知并主张审理人员王某与涉事人员存在特定关系,“法律规定审判人员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的,应当自行回避”,然而提交的回避申请被法院以“超过举证期限”驳回。2025年喀什某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,核心理由是:“即便存在名义承包、实际代管,也不影响合同效力认定,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应受保护。”
值得注意的是,法院采信张某某提供的70万元借款凭证和彭某的100万元借条,却对胡先生提交的市场价格以“系案外人合同”为由拒绝采纳。“2022年收购价每公斤6元,这是公开的市场行情,”但该证据未能纳入法院认定范围,更让他们疑惑的是,白某某在2020-2022年间涉及多起执行案件,乌鲁木齐某法院的查封裁定显示她已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,此时将土地低价转租给亲友的行为,在他们看来可能涉及财产处置争议。
喀什某法院工作人员建议胡先生“向白某某主张赔偿”,他反映追偿存在现实困难:“白某某现在连村委会的承包费都让张某某代交,我上哪儿找她要钱?”这种“实际控制人”的转变,使他们的投资款回收面临实际困难。
四年诉讼耗尽了胡先生的积蓄,2025判决书送达时,他正在乌鲁木齐打工凑诉讼费。
胡先生的代理律师指出:“张某某作为亲家、彭某作为好友,相关方对合伙关系或应知晓,且合同约定价格显著偏离市场价格。”本案的核心矛盾指向两点:合伙人擅自处置共有财产是否构成侵权?显著偏离市场价格的转租合同效力如何认定?现行法律要求“转让合伙财产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”,而法院基于合同有效性作出裁判,司法实践中合同效力与合伙权益的平衡机制,成为解决此类纠纷的关键。
来源: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919068738478671172

(本文基于当事人陈述及公开资料整理代为发布,如有不实言论我们不承担法律责任,如有雷同纯属巧合,侵权请联系更改。)
(责任编辑:314127396)